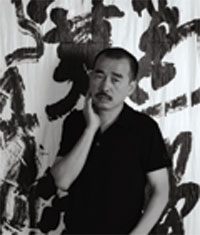
陈侗|文
陈侗,教师、画家、出版人、批评家、博尔赫斯书店及其艺术机构负责人。
游戏与其他词搭配,可以产生多个意思,经常出现的有:游戏机、玩游戏、游戏人生、语词游戏、猜谜游戏、填字游戏、笔墨
游戏(简称“墨戏”而不是“笔戏”,这说明游戏的到达点很重要,就像笑话之所以叫做笑话,是必须使人笑,不能只是说的人自己笑)、感情游戏(与“戏弄感情”有所不同)、性爱游戏(儿童不宜!)。
以上除了“游戏机”、“玩游戏”与儿童有关,其他都属于成人干的事。而且成人也用游戏机玩游戏,这说明成人比儿童更需要游戏。至于儿童对待游戏的态度,大概就跟成人对待工作差不多,因为儿童吃饭睡觉之余,就只知道玩游戏。当然我说的“儿童”是指“学龄前儿童”,他们虽然不太懂得游戏的奥妙(例如捡到一个保险套以为是气球),但他们的特点是什么都能当成游戏,不一定非得有器具和规则。最明显的这方面的例子是从背后蒙住同伴的眼睛——猜猜我是谁,这样的动作发生在成人之间好不自然。
小时候我玩过的游戏都与“战争”有关,例如玩手枪、抓特务和造炸药。别以为这是当时政治宣传的结果。有一点点关系,但不全是。看看现在孩子们喜欢玩什么电脑游戏就知道了:16 比 9 的显示屏上,一个美国大兵端着枪进入某个村子乱扫一通,而玩游戏的人,由于跟在枪的后面,总是不知不觉把自己虚拟成一个刀枪不入的勇士。根据这一点我们可以推断:战争在任何时候都属于幼稚者的行为,但战争不属于游戏,它的目的性太强。
细想起来,我的战争游戏都是独自进行的,就是迷恋手枪和根据对硫磺、硝石和木炭的错误理解去研制炸药。只有遇到竞赛性游戏——例如“拍烟纸”——才会和同伴一起玩。可是我们还得想到一点:像烟盒这种东西也是成人世界的丢弃物(我又想起了垃圾堆里的保险套),儿童很少玩属于自己的东西,除了开裆裤里面的小鸡鸡。
当我们说“幸福的童年”时,指的似乎是:完整的家庭(妈妈爱爸爸,爸爸爱妈妈),有吃有穿(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无病无痛,有人疼有人爱,发育正常和玩得开心。有几个会认为能够像成人那样看事物、想问题也能带来幸福感?还真有:我曾经听到一个编辑讲她的孩子才几岁就特别关心政治,从国家大事更替到妈妈单位的争权夺利,无一不晓,还说“妈妈你为什么不当局长啊?”;最近又听说一个三岁孩子喜欢看新闻联播,更是出奇得不得了,长大了不在台上坐也会是拆台的料。在所有人看来,成人世界就是孩子们的游戏世界。相应地,儿童世界也是成人们的游戏世界,因为我们是看到了儿童世界的非功利才把它作为游戏来玩的。
当然也有一些成人游戏难以界定是否与儿童世界有关,例如买彩票、炒股、赌博和打麻将,它们看似属于“八小时之外”,但都是有利可图的,更别说挪用公款去炒股最终还是要回到严酷的现实这种风险。只有麻将,好像除了运气,还带点无等级色彩:九万并不比一万大,白板也能决定输赢。相反,孩提时代玩“拍烟纸”,我们是讲贫富贵贱的,凡是卖得贵的烟,烟盒就显贵,能用便宜烟的烟盒赢得贵烟的烟盒,带来的是打土豪分田地般的快感。
另一些成人游戏流通于文人墨客之间。例如你出上联我对下联,你画一块石头我画几根草,名曰“雅集”。在现代艺术中,“游戏”一词常常作为揭示艺术本体意义的替代词被提出来,它是对现实主义的反抗。在观念之外的游戏,倾向于技术上的稚拙化,刻意模仿儿童的观察与表达。于是,不懂得深究其中道理的成人看了,会大声地说:“这连我小孩也画得出来!”事实上,儿童在他不知道什么是绘画的情况下所画的画是很可爱的,但是长大后学习了成人的一套观察和表现手法,所画的东西就基本僵化了。而成人艺术家学习儿童,则类似于把自己灌醉,一心一意返璞归真,骨子里还是成人的一套理解和策略,即带有功利目的的游戏,而且也只能在成人世界里流通,所以不关儿童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