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渔|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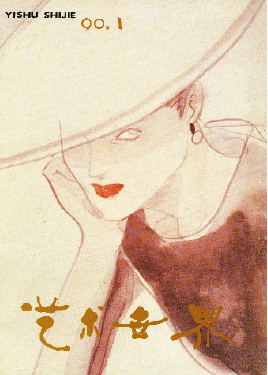
在一本艺术杂志评选的2008年度媒体中,《艺术世界》被认为“是元老级的艺术媒体,也是一个依然保持着年轻精神的综合性人文杂志”。一本创刊于1979年的杂志,年届而立,就已在艺术领域成为“年轻的元老”,得益于天时地利人和。但元老并非天生就是元老,无论是谁,在少年时代都躁动过、孤单过、虚妄过,90年代的《艺术世界》同样如此,像一个少年,拥有各种青春期症候。 90年代初的《艺术世界》像是一份群众艺术馆的文艺杂志,更像是一份校园刊物。在撰稿的作家名单中,我看到王润滋的名字。现在很少有人知道这位作家,他的文章《卖蟹》曾经选入中学语文课本,主人公是一个卖螃蟹的小姑娘,整篇文章主要讲她如何将抢手的螃蟹卖给一个贫困的老大爷,老大爷的老伴患了绝症。我一直认为这篇文章应该入选思想品德教材,入选语文课本比较勉强,由他来给艺术杂志撰稿,那就更加勉强了。再看看栏目名称,1990年是“作家谈艺”、“导演谈片”、“艺术鉴赏”、“艺术纵横谈”、“艺术家一瞥”、“艺术比较谈”、“艺海漫游”、“影视面面观”、“青年与艺术”、“美与生活”、“谈艺篇”;1991年几乎没变,少了“美与生活”、“谈艺篇”,多了“导演手记”、“艺术与人生”;1992年也大致如此。一本艺术杂志的栏目设置如此没有艺术趣味,实在是具有自我批判精神,如同那些美学教材,既唤不起审美也唤不起审丑。再看具体内容,无所不包,甚至有《二胡歌手—周冰倩》、《第一次参加国际魔术大赛》、《素描赵丽蓉》和余秋雨的《关于赵本山的随想》,几乎成了“曲艺杂谈”。我对周冰倩、国际魔术大赛、赵丽蓉、赵本山没有反感,但是看不出他们和艺术有什么关系。或许,可以这样解释,把周冰倩和国际魔术大赛放在同一种杂志里,把赵丽蓉和赵本山看作艺术,这本身就是一种艺术行为。没错,在杜尚之后,没有什么不是艺术。 1993年栏目名称出现变化,实行了“双轨制”,比如在“艺术家一瞥”的后面加上了“艺术家风情”,还新开设了“摇滚天地·开眼界”等栏目。我把这种栏目“双轨制”理解为渐进改革,为了在不同趣味的读者之间获得平衡而采取的权宜之计。也有一些栏目难以理解,比如“风景线·艺术风景线”,两者很难构成并列关系,也没有对称美,或许仅仅是为了符合“双轨制”的体例而设立。尽管杂志依然刊登一些与魔术等有关的文章,依然无所不包,会涉及MTV、广告、流行歌曲,但是多以文化分析的方式进行讨论,不再是单纯的印象记、随想。尽管1994年栏目再次恢复单轨制,但是作者阵容的多样化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陈家琪、吴亮、李公明、刘大鸿、孙甘露、陈东东、王寅等具有独特书写和绘画方式的作者陆续登场,其中一些出现于1992年第3期,这种变化或许与“南巡讲话”有关。不管什么原因,我更愿意假设自己在这段时间遭遇《艺术世界》,因为那时正值我的高中时代,也是一个少年睁开眼睛看世界的时候。王寅的诗歌,我中学时代曾有接触,对那首《想起一部捷克电影想不起片名》印象深刻。这要感谢九叶派诗人唐祈主编的《中国新诗名篇鉴赏辞典》,当时王寅不满30岁。那个时候,入选“名篇”并且“辞典”者,多半墓木已拱,或者行将就木,唐祈却将一大批正值水木年华的诗人选了进去,或许是因为九叶派也是一出生就风华正茂。第一次知道孙甘露,是刚进大学时,在海报栏里看到一位“著名先锋小说家”的讲座信息,自认为见多识广的我居然闻所未闻,这很是挑战了我的知识结构。虽然与上述这些作者后来一一相识,有很多交流机会,但如果在睁开眼睛看世界的时候,能够看到《艺术世界》,能够集中读到他们的文章,我的世界可能会更开阔一些。更何况,那时的《艺术世界》还介绍了很多遥远的如同另一个星球上的事情,诸如文德斯、朋克摇滚、伍迪·艾伦等等。如果一本杂志的“少年史”和一个少年的“杂志史”产生重合,那是多么美妙的事。
随后的《艺术世界》,基本是渐进改革,总的趋势就是减少文艺腔。这与一个少年的成长史是一致的,文艺腔就像青春痘,在少年的时候即使触目惊心,也可以原谅,等到成年之后,偶尔有一两个,也难以容忍。有些文章,现在单独看来仿佛明日黄花,当初却是鲜花怒放。1998年第1期李幸的《中国电视四大病》曾经触动《新周刊》主编封新城,他当时就让编辑找到作者,做了一个批判中国电视的报告,这个选题也“开启了《新周刊》对中国电视整个的评价体系”。“《新周刊》从这样一个弱智中国电视之后以及后面杂乱电视专题以后出了中国电视节目榜,从1999年到2009年整整十年了,一本杂志对电视指手划脚,并且把所有的电视大腕请到一起,只有我们《新周刊》能够做到。”封新城这样回忆。 中学教育告诉我们:量变是质变的必要准备,质变是量变的必然结果。1998年第5、6期合刊,主编小心翼翼地宣布改刊,杂志将做成全彩版。今天看来,这种小心翼翼甚至有些讽刺,一本艺术杂志难道不是理所当然地应该全彩,应该铜版纸么?可是在当时,尽管杂志不断宣称改版如何受到读者欢迎和支持,但我相信,反对的声音一定不会少。至少我在网上,在10年之后,依然看到有网友表示自从那次改版之后就不再订阅《艺术世界》。杂志选择在年底而非通常的年初改版,因为年底正是报刊征订的时候,订户可以根据已经改刊的杂志决定是否继续订阅,不是在新年突然拿到一本面目全非的杂志。年底的合刊还使得杂志社和订户都无需另外支出,因为杂志定价从6元涨到12元,两期改刊前的杂志恰恰等于一期改刊后的杂志。这些全彩的《艺术世界》没有我在2000年看到的那么思路清晰、立场坚定,但是仿佛经历了成人仪式,已经呼之欲出。 伟大的80年代,平庸的90年代,但就是在这平庸的90年代,《艺术世界》长大成人,迎风而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