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克里斯蒂安·史蒂西(Christian Schittich)正在德国慕尼黑的办公室里和同事一起制作下一期的杂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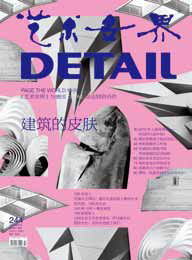 | 关于“艺术知世界”的一些感想
对于今天的专业杂志而言,很有必要打开自己,进行交流,不仅超越国界,而且也要跨越邻近领域的界限。这对文化领域的杂志而言尤为重要。可惜的是,文化常常屈居经济利益之下。
因此,《DETAIL》杂志社十分赞同来自《艺术世界》杂志的倡议,将 2010 年在上海举办的世博会(这个无比精彩也很商业的事)作为契机,通过 Page the World“艺术知世界”这个项目在文化层面上做一次深度的思想交流。
对于一份来自中国的杂志,来自一个那么长时间和外界少有接触并且思想自由常被限制的国度,的确是有必要打开自己。这种必要性却不被视为理所当然,而且常常被忽视。所以我们对《艺术世界》杂志的同行们所表现出的勇气和坦率感到惊奇,并感到十分欣喜。只有通过直接的交流和真正的合作,才可能超越界限,物理的界限,以及思想的界限。
《DETAIL》杂志社很高兴能够在这个项目中展示建筑的一面。这不仅仅是因为我们在全球是建筑类的领袖刊物,而是因为建筑在所有艺术种类和文化体系中具有特别的意义。建筑是用来使用的,必须考虑实际的功能和经济效用。如今建筑正在前所未有地影响着我们的环境和我们所在的城市。建筑有一种双重性,至少在现代建筑中,建筑围绕着人们和他们的生活。在中国,在长期的匮乏之后,如今迎来了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但是这种急速发展常常以牺牲建筑的质量为代价。所以我们希望可以展示一些好的例子,以期人们能够作出一些改变。
Page the World “艺术知世界”是一个令人振奋的、十分吸引人的项目。这个项目应当在世博会之后继续前行。
—— 克里斯蒂安·史蒂西(Christian Schittich)《DETAIL》杂志主编 |

玛格南摄影社前任主席 René Burri 所拍的编辑部合影。Photographer: René Burri
(Former President of Magnum)
从左到右: René Burri, Lars Willumeit (摄影总监/Photo Director), Themba
Mabona(实习生/Trainee), Anina Gross(专员/Special Forces), Oliver Prange
(出版人/Publisher), Oliver Burger(出版总监/Publishing Director), Franziska
Neugebauer(艺术总监/Art Director), Arnold Speck (财务总监/Finances),
Stefan Kaiser (主编/Editor in chief), Noemi Wagner(实习生/Traine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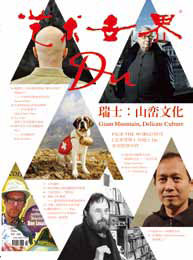 | 一次很有趣的经验
当我们在四月份的时候,《艺术世界》前来询问我们是否有可能合作,我们一开始觉得这是个玩笑——用中文出版我们的 Du 杂志,要发行 6 万册(我们的月发行量才 1 万 5 千册)。自 1941 年,Du 杂志在瑞士、德国和奥地利以德语出版,现在尽然还在中国!这个精彩的国家!而且这恰好是在我们即将满七十周年的时候!这实在是个太好的机会了。后来在和《艺术世界》沟通之后,我们很快就抓住了这难得一现的机会,并充满自豪。
对这次合作的结果,我们振奋极了!这感觉实在太好了,看到我们费尽心血的杂志在中国用中文出版了(虽然我们没法看懂中文)。这个合作的主意真是棒极了,和《艺术世界》的合作非常愉快,也是很有趣的经验,我们希望我们很快就有下一次合作。我们衷心祝愿《艺术世界》继续成功,并对未来的长期合作关系感到欣悦,因为将来在中国也会继续有人成为热爱 Du 杂志的读者。
—— 奥利弗·伯格(Oliver Burger ),Du 杂志出版总监 |

Parkett 的主编 Bice Curiger 女士与嘉宾,以及《艺术世界》杂志工作人员合影。
前排左起:谭昉莹、张小船、龚彦(《艺术世界》杂志主编)
第二排:伍忱、王海凤(翻译)、亦岑、钟瑾
第三排:王晓渔(嘉宾)、顾杏娣(《艺术世界》编辑部副主任)
第四排:吴亮(嘉宾)、Bice Curiger、沈奇岚(《艺术世界》编辑部主任)、蔺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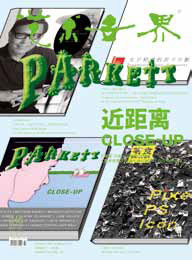 | 世界和世界的相逢
“Page the World”,艺术知世界,是一句魔法咒语,召唤着世界上最优秀的艺术媒体,来到《艺术世界》杂志上,呈现给中国的读者。
Page,是定格,是翻页,是呼唤。
我更愿意把“page”理解为呼唤。“艺术杂志可以并可能做什么”这个问题,是和
Parkett 合作之后,我渐渐有了一个清晰的答案。
就像 Parkett 的主编 Bice Curiger 在今年九月来到《艺术世界》杂志社与我们的嘉宾举行座谈时所说的:“智力上的辩论和交流对艺术至关重要,艺术之所以能作为艺术存在,正在于我们能谈论它、评论它。否则,艺术就只是展品,是物件,无法成为艺术。无论是在电子时代还是过去的时代,都应该有一个平台,能够让人们交流的机会。”——这是一份艺术媒体的自觉,是一种独立思想的信念,以温和但不妥协的态度,默默持守着一流的思想质量和艺术品格。这是 Parkett 坚持了 25 年的原则。
可以说,和Parkett的合作让我获得了一种作为艺术杂志制作者的自我意识。我从来没有想过一份杂志会对自己的影响如此深刻,以至于回国之后,我被召唤到了《艺术世界》杂志。对此,我对命运的偶然和必然心存感激。
此时此刻,Parkett 的出版人 Dieter von Graffenried 在去迈阿密艺术博览会的路上。他的下一站是首尔,Parkett 的下一场展览将在那里举办。Parkett 的主编 Bice Curiger 刚刚从南美洲回到苏黎世,作为 2011 年威尼斯双年展的总策展人,她在忙碌地筹备着半年后要开幕的盛会。和他们能够建立友谊,要感谢这句魔法“Page the World”。
Page the World, 是艺术杂志人的惺惺相惜,是世界与世界的相逢。
世界那样宽阔,我们肯定会再相逢。因为在艺术的世界,我们被同样的命运召唤着。
—— 沈奇岚,《艺术世界》杂志编辑部主任 |
张小船(编辑): 这项目挺好,介绍国外优秀杂志的内容给国内读者,算是一个桥梁(还有朋友专门打电话来赞美);当然,也是镜子。好的杂志就应是一平台,不要有太多欲望,老老实实呈现。挑选的眼光本身就是态度。 许梦琦(美编): 我很欣赏 Page the World 项目合作的几家杂志的版式设计,尤其是 Du 杂志,图文比例恰到好处,很不简单。但我想,《艺术世界》杂志不会去复制别人的模式,而应该走自己的道路,创自己的风格。 胡俊(复旦视觉艺术学院老师): “Detail”这期杂志主题很明确,文章、图片选择与时代同步,集中传达了当今最重要的建筑理念,很富有感染力。我并 非艺术或建筑的圈内人士,平时和数字打交道,但我认为这期杂志给圈外人士的触动点更多,带来理性之外的一种冲击,所以这才叫“艺术知世界”,而不是圈内人士自己的世界。 谭昉莹(编辑): 偶遇一圈内同行,盛赞了《艺术世界》与《Detail》杂志合作的那期。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项目,把我们的视线和全世界优秀的艺术媒体拉到了同一个纬度,也让读者能够在纸上欣赏那些经过沉淀、经过锤炼的文章。以后还有合作机会的话,希望可以更深入挖掘那些创作背后的“猛料”。 丁乙(艺术家): 我觉得 Page the World 提出“媒介共生”这个概念非常新颖,国内杂志介绍国外艺术往往只是信息类,而Page the world 做到了深度、广度和整体把握,它涵盖了文化与艺术的不同侧面,这种交叉性切合了现在读者的需求。艺术跨界越来越普遍,做艺术的人需要和不同区域、不同类别的媒介联接,这是国际化的思考方式。 令狐磊(杂志人):
经由艺术世界的 Page the World 计划,我终于可以以中文阅读的方式与我久仰的 Du 杂志见面。我是在地铁里读到这一期的,因为注意力过于集中还为此错过了站。里面对杂志的见识与全然自信笃定的信仰,让我可以真正理解缘何这本杂志可以从 1941 年至今历久常新。而那篇“某些邻国我尤其不喜欢”的意义和观点也让我叹服杂志作为一个社会工具可以真正地具有力量:让读者进入全然未到过的时空,还心存感激。
伍忱(编辑):
了解世界有很多途径,Page the World 是其中一种,一页页翻进去,以谦逊好奇的姿态去了解国外同行的眼光和工作角
度,然而最终不只是观赏,总要回过头来看自己,身处北纬31 度的我们能为这个世界提供一个什么样的切面?
王晓渔(评论家):
在共识中寻求差异,在差异中寻求对话。没有共识的差异,是断裂;没有差异的对话,是自言自语。艺术知世界,关于对话的邀请。
丁宁(编辑):
Page the World 之“Du 杂志:瑞士之山峦文化”视艺术本体如宗教神明,采撷每一块尚未羽化的艺术切片,尝试逾越地域与语言的限制,无远弗界般地伸向每一处偏僻的山野。观者在恍惚中被带入云游般的神秘旅程,一面探访档案博物馆的始末原委,一面领略阿尔卑斯山脉的高耸入云,甚至住进了艺术家架设的虚拟旅舍之浪漫客房。这一切并非梦幻,而是眼前的真实。
顾婧(编辑):
《艺术世界》与国外艺术媒体的“共生”项目,首先遇到的是“水土不服”的问题。为此杂志社的同仁们颇动了一番脑筋,从视觉设计到文字编译,力图在保留西方原味的基础上,使之为本土读者所接受。和所有其他事情一样,最难的便是寻求平衡点,对于 Page the World 来说,做到雅俗共赏、融贯中西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亦岑(编辑):
处处字母当道的这几个月,整个编辑部把世界铺在纸上,用中文“平面”了建筑,“文字”了艺术。更多地作为读者的我很满足。两个月前,看到读者在豆瓣上给《艺术世界》留言“老而弥新”时,我很欣喜;2011 年的 Page the World 会给出怎样的惊喜?把杂志中的世界铺进电视?我也一样,很期待!
蔺佳(编辑):
对我来说,与《Detail》合作的那期是最难阅读的。我一度怀疑,“建筑的皮肤”是否适合大众口味,会否太过专业艰深而吓退读者。前几日在编辑部接到一个读者电话,读者说非常喜爱与《Detail》合作的那期,询问能否通过我们杂志社继续订阅《Detail》。原来,我眼中的冷门是别人眼中的热爱,一件小事让我豁然开朗。
沈奇岚 (项目总执行):
Page the World 是一次过瘾的冒险。当主编对我说:“去和这些媒体谈谈看吧!”我想,这真是有难度,要说服别人白白和我们分享他们最好的内容。可是,居然真的有人愿意,慷慨分享,倾尽全力。
参与 Page the World 项目,对我而言是一场学习之旅,穿越欧洲大陆,和世界上最出色的艺术媒体一同制作共生杂志。记得网上有过一个以物换物的游戏,有人交换了几十次之后,用一枚回形 针换到了一幢别墅。从最初的一个想法,到如今这样四本或许具有历史意义的杂志,我真是有同样的感觉。——真是太幸运了,真是太过瘾了。另外,这也坚定了我的信念:只要是好的想法,一定能找到不遗余力的支持者。
顾杏娣(编辑):
我同意《Purple》创办人 El ei n Fleiss 的观点:“我不认为杂志能为社会带来任何冲击了﹐但我只是想保存一些声音﹐即使这声音既脆弱又小众,这声音说的是‘我们还未被完全击败﹐我们还未死去﹐我们有不同的想法﹐别把我们的世界看成是大部分媒体上呈现的世界﹐ 别把我们的生活看成是大部分人倡导的生活’”。Page the World 项目或许能成为一个全球优秀杂志共生的好方法,把那些脆弱的声音收纳到这个项目中来,然后把《艺术世界》卷成喇叭状,放给全世界听。
张恩利(艺术家):
一本杂志让人看和购买很容易,一本杂志让人喜欢且去收藏非常不易。喜欢 Page the World 这个项目,特别是对我这种不懂英语的人。
木木(编辑):
与 Parkett 杂志合作的那期“Close-up”,齿线证明了能够被PAGE 的世界的丰富性。齿线标示出两本杂志开本的差异,更完成一次共生与界限的被突破。不同的世界在齿线两侧相望,被拉近,再被审慎地加以区别,齿线让读者介入和判断。
张达(艺术家、设计师):
喜欢这一期艺术世界和瑞士杂志 Du 在一起的 Page the World,因为里面有对 Du 杂志的老编辑胡戈·罗切尔的访问和对 Du 现任主编的访问。看胡戈谈 50 年间的办刊感受很有意思。对比老编辑和现任的采访,有很多感慨。这期里还有我喜欢的建筑师卒姆托的访问。通过《在档案工厂》了解策展人哈罗德·乌尔美的工作也非常有趣。
龚彦(项目总策划,主编):
一个记者听完我对 Page the World 设想后在 MSN 上留言:“首先请告诉我怎么能让别人觉得这不是一个笑话?”不知在历经了 11个月后,这个掷地有声的“笑话”是否已足以砸碎胆怯并具备了感恩的能力,而那个我们创造的优雅的“Page”姿势,是否也能欣然褪去媒体的霓虹,回归一种寻常的观看之道?
从 2010 年 1 月 11 日我给杂志驻德法国记者发出的第一封信,到 3 月 1 日 19 点 49 分,兴奋地宣布 Page the World(缩写 PTW)名称的诞生,到三八妇女节收到第一封拒绝信,再到之后一系列的 Yes。我们在地球上做着脚注,一如 PTW 的 logo——一个折了角的地球;我们用最简单直白的方式进行“编辑”,拒绝“解释”,一如 PTW 的海报—— 12 个从 4家合作媒体 logo 中摘取出来的字母。
“共生”是一份邀请,寓于别人的世界是一种双重享受。PTW 是一个超越灵感的编辑过程,无数的细节让我感受着每本杂的背后的人,学习如何编辑一张没有涂层的白纸,如何通过遏制欲望建立一个真实广阔的平台。
刘欢(设计总监):
一个朋友说纸媒已经没意思了,一个朋友因为外刊中文版创刊急寻设计师。书或杂志带来零距离的分享和想像,书本的收藏更加满足人的原始私欲。放下一段时间,再回头看看 Page the World,摸得着的回忆会让我们记忆犹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