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龙|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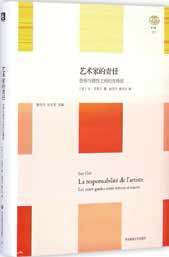
《艺术家的责任》
La responsabiliré de l'artiste
作者:【法】让•克莱尔(Jean Clair)
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副标题:恐怖与理性之间的先锋派
译者:赵苓岑 / 曹丹红
出版年:2015-3
页数:178
定价:38.00 元
20 世纪上半叶的法国无疑是世界的艺术之都,也是美国艺术家的圣地。当 1913 年“军械库展览”在纽约开幕时,以法国为中心的欧洲现代艺术震惊了依旧陷溺于文艺复兴与古典主义时期的美国艺术界,引发了迈耶·夏皮罗所谓的“美国艺术的转折”。1917 年法国人杜尚更以小便池《泉》改写了美国艺术史。然而,半个世界后,法国艺术却遭遇美国艺术的全面颠覆。格林伯格在 30 年代对欧洲艺术中心论依旧逊言恭色,50 年代后却洋洋自得地将美国抽象表现主义推崇为艺术史的巅峰,而这一戏剧性的转向恰是历史嬗替的表征。伴随二战后美国无可匹敌的文化宰制力,法国艺术逐渐沦陷为附庸,在全球艺术格局的地位亦随之式微,就此导致了法国人文主义危机,进而引发 90 年代法国当代艺术之争。让·克莱尔,撰写《艺术家的责任》的作者,即为论战核心人物。
作为法国艺术史和艺术批评的巨擘,克莱尔成就非凡,他于 2008年当选法兰西学院院士,跻身“不朽者”行列。其深受列维–斯特劳斯与列维纳斯的影响,以人文主义学院派自居,猛烈批判现代性,指责现代艺术对西方文明的摧残。同时,他追随斯特劳斯的文化多元主义,抨击法国艺术的美国殖民化,主张回归本土性、差异性,但也因此困囿于斯特劳斯思想中隐含的欧洲中心论桎梏。他曾指责现代艺术放弃美学价值而堕落为“恶心”(disgust),贬斥当代艺术为掩饰自身的平庸性而故意曲解杜尚。这一观点引发了丹托的激烈抨击,成为“美的滥用”之典型。
《艺术家的责任》是作者对其另一著述《论美术的现状》的基调延续和精密化论证。在书中克莱尔聚焦现代艺术的责任危机,彰显其作为列维纳斯信徒的哲学立场,并揭橥了现代性包含的激进理性主义与非理性的浪漫主义间存在二元对立,而肇端于此的先锋派与极权主义则存在本质关联,从而沦为政治恐怖的帮凶。二战后抽象表现主义驱逐具象与意义,美国主宰的普遍主义霸权否定文化多元性,造成文明的崩塌和逻各斯的破碎。他也指责法国中央集权的官方艺术体制与政治干预难辞其咎,抨击博物馆系统助纣为虐。就哲学史而言,他对现代性的这种清算可被视为德法之争以及英美–欧陆之争的双重缩影。
正如鲍曼在《现代性与大屠杀》里所言,犹太人大屠杀是现代性的本质产物,源于工具理性对道德责任的褫夺。克莱尔对“艺术家责任”的论断与此相契。其直抉本源,引他者伦理学为奥援,借助马丁·布伯的“我与你”(I and Thou)和列维纳斯的“他异性”(alterity),从哲学本体论层面进行阐述。如列维纳斯所言,“意义是他者的面孔,一切诉诸文字的行为已经位于语言最初的面对面关系内”,克莱尔由此主张阿多诺关于“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论断应理解为重新澄明图像与语言,返归本源的“面对面”(face to face)主体间性。图像的末日实即道德的终结和人类的灾难。故而具象艺术本质上是伦理行为,他者之脸是主体内部的绝对他异性之显现,对此的辨认和图像表现意味着对他异性的尊重和凸显,对本源的呼唤和回应,此即艺术家的根本责任。
先锋派和抽象艺术由于否定他人之脸,背弃了道德责任。通过具象与责任的概念转换,克莱尔将列维纳斯的“面孔”与艺术的具象相联结,以此克服现代性的危机,既远离传统摹仿论的陈词滥调,也澄清了其“回归写实”主张的本质内涵,指出了艺术的救赎之路。埃贡·席勒的“艺术不可以现代,艺术回归本源”恰是本书最好的注脚。然而,当克莱尔接受采访并表示“人物的具象是西方人文主义、宽容和传统价值的最重要标志,抽象则与反偶像、偏执、专制和东方相联系”时,他依旧难脱欧洲中心论的窠臼。这种保守主义的立场彰显其责任伦理论述的不彻底性,存在意义自我消解之虞,并易令本书的论证陷入“海德格尔与纳粹”问题的思想泥淖。
纵然如此,借助《艺术家的责任》,我们确能领悟克莱尔的艺术主张绝非皮相之言,亦可知作为总策展人的他将 1995 年威尼斯双年展主题定为“Identite et Alterite”的题中之义。由此反求诸己,反思中国当代艺术的责任问题,并重新审视 90 年代受克莱尔影响而兴起的中国“具象表现主义”,亦将具有异常深远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