栾志超 | 文
【节选】
什么是进步?
大概是文字工作者:进步就是在向前走的时候回头看觉得前方更有希望。
已婚的女人:进步就是宝宝出生,一家三口。
男艺术家:进步就是女朋友挣钱养我,我们俩结婚。
抱着宝宝来的妈妈:进步就是……(深情地望着怀里的宝宝)四五十岁看破红尘的妇人:进步就是放弃一些东西。
蔡春芽(《我故乡的四种死亡方式》的导演):进步就是人类创造的词语,我们用脱离了固定的含义来解释它,还很受常识的影响。
刚参加完798奔驰发布会盛装打扮的尊贵夫人:进步就是升职加薪,事业有成,家庭和睦。
肥胖的富商:进步就是挖煤挣钱。
——采自魏易药
陈晓明(成人组),31 岁,目前是个大拇指停不下来的手机写作者,有个正在试用期的笔名叫耳鸣。 魏易药|图片提供
“什么是进步?”(What is Progress?)这是提诺·赛格尔(Tino Sehgal)为《这个进步》(This Progress)这件作品挑选阐释者(interpreter)的时候问面试者的第一个问题,也是观众一走进入口必须回答的一个问题。出生于1976年的提诺长着一张娃娃脸,有一位系统阐释了他作品的艺术史家妻子和一个两岁多的儿子。他在柏林工业大学和埃森大学学的政治经济学,在艾森福克旺艺术大学学的舞蹈,还在杰罗姆·贝尔的舞蹈团工作过。但他始终认为仅有把政治和艺术结合在一起之后,政治在这些实践中的重要性才会彰显出来。提诺创作的第一件艺术作品是《不要让事物到你眼前来,把布鲁斯、丹和其他人的作品跳出来》(Instead of Allowing Some Thing to Rise up to Your Face Dancing Bruce and Dan and Other Things ,2000)。在这件作品中,一位舞者在美术馆的空地上缓慢地移动,做出丹·格雷厄姆和布鲁斯·瑙曼录像作品中的动作。类似这样的作品提诺后来又创作了很多。如《这是宣传》(This Is Propaganda,2002),在这件作品中参与者打扮成博物馆安保人员的样子反复地念着“这是宣传,你知道的,你知道的”;《这是交易》(This Is Exchange ,2002),观众和参与者就市场经济进行讨论,然后获得一美元;《这是新》(This Is New ,2003),这件作品要求博物馆的员工从当天的新闻报纸上找到头条然后再告诉观众;《这太当代了!》(This Is So Contemporary! ,2004),演员们打扮成博物馆安保人员的样子,突然在观众面前开始跳舞,嘴里唱着:“噢,这太当代了!当代!当代!”……
提诺把自己的这些创作称为“ 情境建构” (constructed situations),其最基本的一点是非物质性。艺术的去物质化从上世纪60年代的当代艺术中就已经肇始。不管是当时的激浪派或是偶发艺术、行为艺术,不管是乔治·马修努斯、道格拉斯·胡埃贝勒,还是小野洋子,他们当时的作品就已经动摇了创作者的权威性以及艺术作品仅能以一种具体的、实在的物的形式来呈现的传统。但是,仅仅从形式上来看,提诺创作中的非物质性或者说去物质化也不只是否定创作者、否定实物、否定白立方这么简单。在提诺这里,创作的材料变成了纯粹的人,没有任何实体的物参与其中。他把作品的实施方式告诉参与者,然后由参与者来实施。但是,提诺同时又将他的作品和表演也区分开来。因为和偶发艺术或是行为艺术不同,在他的作品中并不存在演员和观众,表演和观看——他去除了演员和观众之间的距离,人人都是参与者——只有观众也参与其中,作品才会发生。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每一个身体都是平等的,观看、体验也是平等的。而且,作品始终都在进行之中,始终都是未完成的状态。这也和有具体的开始和结束的表演区分了开来。提诺的作品不仅仅在呈现的形式上是非物质的,他还禁止对他的作品进行任何照片、录像或是其他视觉形式的记载。此外,提诺的作品还采用公证人在场的情况下做出口头协议的形式来交易。
魏易药(青年组),18岁,在参与这个作品之前,对提诺·赛格尔一无所知,对当代艺术也没有任何想法,只是个偶尔读读诗歌、看看电影,反感体制的中学生而已。刚从国际高中毕业,准备去美国读书。因为托福成绩不太满意决定次年再走。对未来的方向很明确——数学系,双修摄影,辅修设计,研究生读建筑。现在多了一个想法,就是艺术。魏易药|图片提供
然而,尽管提诺的作品从始至终都是去物质化的,但他又强调自己作品发生的情境和传统视觉艺术的展览情境必须相同——博物馆或者美术馆、和雕塑、绘画、录像等形式的艺术一样从开馆到闭馆的展览时间等等。因此,如果说艺术生态和社会化大生产分享同样的模式——艺术家在观众看不到的地方创作作品,作品在升华了的白立方中展出;真正的劳动被隐藏,观众最后看到的是一个升华了的、被赋予各种过剩价值的物——那么,提诺对艺术的去物质化最终就是对升华和崇高、对价值、对拜物教的否定。物的伦理、由物产生的消费导向在这里消失了。提诺把创作的空间和展览的空间合二为一,从而去除了从物到有价值的物的升华过程;他把创作变成了作品本身,从而使得创作这样的劳动本身成为有价值的——创作因此不是手段或是以物为目标,而是目标本身。物的伦理中要求生产性的消耗,而在提诺的作品中,观众看到的却是非生产性的消耗——阐释者和观众参与创作,却没有任何实体的作品被生产出来;物的伦理把时间和情感都浓缩成了物的附加价值,而在提诺的作品中,观众能够感受到分分秒秒的流逝,能够在一个具体的情境中分享自己的体验。媒体大众时代对我们体验时间方式的改编,在提诺这里得到了修正。提诺白立方中的崇高之物只有身体、身体的消耗、身体的互动、转瞬即逝的体验以及情境。
这或许是提诺选择博物馆、美术馆这样的机构展览自己作品的最重要原因——这里是艺术生态规则的形成之处,这里有着市场经济那双看不见的手。他要在传统和价值形成的地方开始自己的破坏和重建。这也是几乎他所有的作品都以“这个”开头的原因。这个词所特指的独一无二性在解构了景观社会图像复制的同时,也构造了另外一种拜物教——一种自身的、当下的、短暂的价值。提诺曾说,他作品的本质在于他自己的主体性和他人主体性的融合。这或许可以理解为广义的关系美学,而且这一美学贯穿他的作品始终:从他到参与者到观众到评论到有关他美学的知识生产。这是一条仅有其开始却从不结束的单向线,可以绘制出整个的社会网络和一个水平的社会机制。当然,这一点也是提诺作品最为矛盾的地方。他禁止任何人对自己的作品进行任何视觉材料方式的记录,可是他又极度地依赖于文字来描述和阐释他的作品。对语言和文字的依赖从他给参与者讲解作品如何发生的时候就已经存在了。因此,在他去物质化、去生产的地方,也正是抽象的知识生产发生的地方。
什么是进步?如果从艺术史的某个微观的角度来看的话,提诺的创作或许就是进步——他在去物质化这一艺术观念上的推进,他对艺术生态、政治、经济、观看、作者的权威、展览的机制等等的反思。但是,正如他的作品是对情境的建构,他的作品也仍然依赖于情境。他对关系的依赖导致了他作品本身的暧昧。很多时候,我们很难界定提诺的创作是对目前当代艺术语境的利用,还是也仍然囿于这样的语境。并不是每个人都为他的作品叫好——本雅明·布赫洛在 2005 年的威尼斯双年展上看了《这太当代了!》,就说他的作品是“狗屎”——他也是近年才成了当代艺术圈的宠儿,而这部分地也还是仰仗整个艺术圈的机制(在大鳄美术馆和博物馆做展)以及知识圈的运作。
什么是进步?提诺在中国举办大展,这或许就是个“进步”。罗伯特·劳申伯格的大展不过是上世纪 80 年代的事儿,那时候的中国还在“现实主义”的语境当中。而去年年底的时候,有一位日本友人问我有没有去看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的安迪·沃霍尔展和约瑟夫·博伊斯展。他说如果单论看展览的话,他更喜欢呆在中国,因为在东京几乎看不到什么大展;如今在亚洲,只有在中国才能看到很多国际知名艺术家的展览。得益于各种奖项提名,提诺的展从去年年中的时候,就开始吵得沸沸扬扬。展览开幕之后,有观众专门看了很多遍。尽管在中国目前的当代艺术语境中,已经不太可能出现像劳申伯格那样的启蒙效果,但是,提诺的展览也还是成了年度的一个现象。
《这是进步》展览现场的通道,魏易药|图片提供
这个进步
在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的这次个展之前,提诺已经在中国做过展览,并展出数件作品。这次展览展出了他的两件作品:《这个进步》和《这个变化》(This Variation,2012),舞者们在一间黑屋子里随机唱歌跳舞。在《这个进步》这件作品中,观众一进入口就会有一个小孩上前表示欢迎,自我介绍,告诉观众这是提诺的一件作品,并邀请观众和他/她一起参观。在这个过程中,小孩会问参观者一个问题:“什么是进步?”,然后或许会问:“你为什么会觉得这是进步?”在走过一段之后,会遇到一位青少年。小孩会把观众刚才就进步所发表的观点讲述给青少年,然后转身离去,观众继续和青少年就进步的话题展开讨论。尔后,又会遇到一位成年人。青少年简单地介绍刚才的聊天内容之后也离去,观众继续和成年人讨论。最后会遇到一位老年人。老年人会给观众讲一个自己亲身经历的故事,在出口处和观众说再见,并告诉观众:“这件作品的名字叫做《这个进步》。”
和提诺的其他作品一样,如果仅仅是这样描述整件作品的发生过程的话,会觉得简单得发指。但是,提诺的每一件作品在展厅实现的背后,都有很多并未呈现的工作。在每次展览之前,提诺都要花很多的时间来寻找合适的作品阐释者。因此,在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的这场展览,他的两位助手在开幕两个月之前就开始了在中国的招募和排练工作。通过采访,两位阐释者还原了当时的一些场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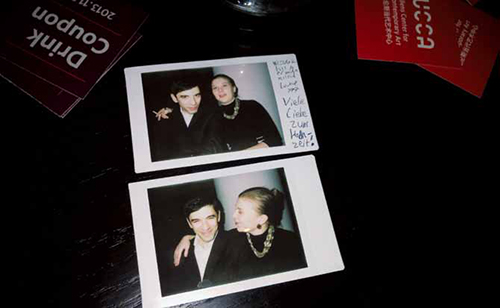
戴德轩(Louise)和陆遥(Descha),Tino的助手,一对很有爱的夫妇 魏易药|图片提供
闭幕时的情景,魏易药|图片提供
● 如何成为作品的阐释者?
魏易药:我是在豆瓣上看到的招募信息(似乎青年组只有我一个是从豆瓣上来的,其他都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或是其他大学的学生。可能跟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有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实习生有关系)。当时面试我的有三个人,比利安娜和提诺的助手 Louise和 Descha。他们跟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什么是进步”。陈晓明:面试我的是提诺的助手大山和陆遥。当时和我一起参加面试的还有另外几个人。我们在一起很随意地聊天,谈自己的生活、工作以及兴趣爱好。后来,提诺的助手告诉我们说,他们就是在这样的沟通中观察我们适不适合参与这个项目。
● 当时的排练如何进行?
魏易药:准确地说,提诺的助手和 UCCA 的工作人员是告诉我们这件作品是如何发生的。训练完全采用口述的方式,不会告诉我们这件作品要表达什么。参观者感受到的是什么,那就是什么。
● 对阐释者有没有特殊的要求?
魏易药:有一些细枝末节的要求,但是都不是强制性的,一般都是“最好不要这么做”。比如,最好不要跟参观者说自己的想法,因为这会让参观者改变自己的想法。对于不配合的参观者——毕竟大多数观众都没有此类的参展经验,不熟悉这种展览模式——最好不要强制他们去跟自己说话,让他们自由行走,他们只是无法参与到这件作品当中来而已。
● 对展览满意吗?
魏易药:有点不满意。因为每个组里的每个人都不一样,并不能按照参观者的类型来分配最合适的阐释者。因此,有觉得这个展览特别肤浅特别没有意思的观众,也有抱着老年人痛哭的观众,觉得阐释者在用心和自己对话。认同差异感是我在这个展览当中体会最深刻的一点。
陈晓明:基本满意。我觉得展览设计的整个路程不够,在观众多了的时候,很多话题只能是开个头就结束了。观众这方面的话,一开始很不喜欢没有礼貌的参观者,后来觉得和“我知道你们想要表达什么”以及想知道“你们到底要表达什么”的观众交流起来是最困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