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化童 | 采访 顾晨 | 摄影
朱大可,学者,文化批评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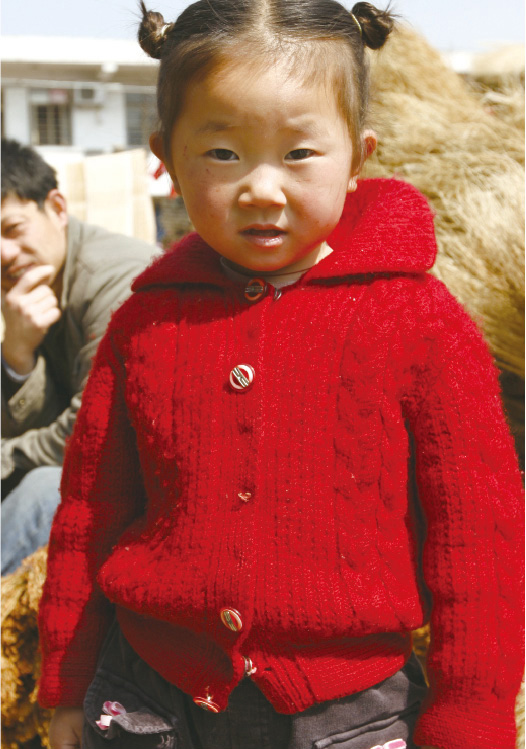
您90年代中期在盛名之下,突然远渡重洋去了澳大利亚,八年之后归国又选择了莘庄作为定居之所。对于整个西方世界的文化来说,澳大利亚处于一个边缘的地位;对于上海的地理环境来说,莘庄也同样是一个边缘地位。这样的选择时逢一种巧合,还是您主动选择了这种边缘的蛰居方式?
朱:这纯粹是一种家庭变故造成的偶然事件。我当时对这个区域一无所知。但它的确比较符合我的个人身份——一个离家出走的游者。严格说来,是我选择了“被边缘化”的道路,并且非常喜欢这种状态。我跟这个城市没有本质的关联。我感觉自己是悬置在半空中的怪物,靠互联网的丝带,微妙地维系着跟土地和城市的关系。 您习惯采取“自我边缘化”的姿态来对抗陈腐的学院体制之中的学术氛围,在绝大部分时间里,并不被主流学界认可,甚至长期在高校中只担任讲师,因此荣获“中国第一讲师”的称号。那么,您对于居住地点的边缘化选择是否和您在学术上的趣味存在某种联系?
朱:当然如此。有人认为我是主流精英,这是一种文化误解。为了捍卫独立言说的权力,边缘化是必要的。它甚至是一种逻辑前提。这不仅是一种趣味,更是一种必要的立场。 除了边缘化的文化身份对于您选择边缘化的地域身份之间有所关联,还有什么原因促使您在莘庄落户?
朱:选择是简单的,但在选择之后,会慢慢发现这里居住了一些类似的边缘人,俨然是一座边缘人的村庄。这种地理上的亲昵性加强了我们之间的联系。每年的某些时刻,我们都会有一些区域性的聚会,跟不同的村民,谈论不同的话题。我能够感到这种文化聚落的价值,我不会轻易离开这座悬空的村落。 您楼上住着学者张闳,两个知名的文化批评家“楼上楼下”,是上海文化圈的一则趣闻。当初你们是怎样作出这样一个决定的呢?
朱:我看中了正在热卖的新梅广场,打了个电话叫张闳来瞧瞧。结果大家都不假思索地付了订金。事情就这么简单。 |